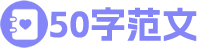“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张枣)
错误,失败,曾经错误的期待——这些经历都和遗憾、懊悔、失望甚至羞耻的感觉相关。尽管谈论那些已经错失的机会和曾经错误的期待不会是太愉快的经历,这些经历却对我们的人格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心理学家Laura King和Joshua Hicks 在许多年的时间里研究那些会让人感到遗憾/懊悔(regrettable)的经历与人格成熟度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个体在成人期,会经历很多目标的改变,这种目标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个体发展的机会。而那些失败了的目标(不再有机会去实现的目标),则被研究者看做“失去了的可能自我”(lost possible selves)。研究发现,人们对待自己“失去了的可能自我”的方式,会影响他们的幸福度、人格复杂度及成熟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每个人成长路上所必经的哀悼——那些我们失去了的“可能自我”。
成长的目标与可能的自我
成长的每个阶段,我们总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有一些或大或小的目标要去达成。
Laura King和Joshua Hicks 认为投入到对目标的追求中能够极大提高人的生存质量(well-being),但追求目标,同时也会给人带去挑战、困难、甚至注定了会有失败——没有一个人可以实现自己所有的目标,以及,我们总会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感到遗憾—— 为那些我们没有机会追求的其他目标(did not pursue instead)。
有时我们需要放弃一些已经显然无法实现了的目标,比如爱上一个不可能的人,但事实上,放弃(disengage from)那些自己珍视的目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它会带来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处境的(负面的)重新认识——期许的未来就是不会到来了。放弃一个目标,意味着自己过去投入的价值不再有回报,意味着接受自己曾经的期待是错误的,甚至意味着要重新评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想要不再被遗憾和懊悔困扰,想要获得自由,个体必须斩断自己对那些目标的恋恋不舍——“它们不再是我的目标了”。
然而Brunstein 和Gollwitzer (1996) 的研究发现,当人们发现目标可能已经无法实现了的时候,比起放弃原有的目标,人们更倾向于付出加倍的努力来企图实现它。这可能就是科学研究对“人多执念”的证明吧。
随着个人的发展,我们逐渐实现了一些目标、发现了一些目标达不到、对有些目标失去了兴趣,目标的转换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发展的进程。 基于目标转变和人格发展的关系,研究者们提出了“可能的自我”理论框架。
“可能的自我(possible selves)”被定义为重要的人生目标的拟人化代表(Markus & Nurish, 1986; Ruvolo & Markus, 1992)。那些“可能的自我”里不仅仅包括了我们当下所追求的目标,也包括了所有与之相关的我们期许的未来。对个体来说,“可能的自我”是一种在整个成年后发展过程中,激励着个体的认知资源。
不同的“可能自我”对我们有不同的意义和重要性。King 和Hicks提出了一个衡量可能自我的维度:“显著程度(salience)” 。“显著的可能自我”,指的是那些长期且频繁出现在个体自我概念中的“可能自我”,它们往往也是个体持续的动力来源。例如,一个医学预科生始终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甚至这个念头每天都出现在Ta的脑海中,那么“医生”就是Ta显著程度很高的“可能自我”。
在“可能自我”的理论框架下,成长被看成不断吸收(assimilation) 和调整(accommodation) 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对世界及自身的理解。当我们的经历符合我们既有的对世界和自我的理解时,我们感到舒服、顺利,这时这个经历就被吸收到我们既有的认识框架中去了。——这个过程就是吸收(assimilation)。
但有时,我们的经历会超越我们既往的认识图式(类似于认识框架,scheme),明明以为可以做到的事失败了,以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原来并不喜欢,等等,这时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认知体系,从而能够解释新的经历。——这个过程就是调整(accommodation)。在调整后,生活再一次变得可以理解。
吸收的过程,往往是实现了当时头脑中的“可能自我”的过程,而调整的过程,则是失去了当时以为的“可能自我”的过程。而失去可能自我的时刻,被Laura King称为“teachable moments”,在这些节点上,我们会问自己“我如何到了这里?”、“我接下来要前往哪里?”这些时刻正是我们获得更复杂、更高级、更有解释力的认知体系的机会。
“如何看待可能自我”和成熟度之间互相影响
心理学家King 和Hicks 对经历过重大生活转变 (transition) 的成年个体(包括唐氏综合症儿童的家长,婚龄超过后离婚的妇女,以及男女同性恋者)进行研究,请他们用叙事 (narratives) 的方式记录他们的“可能的我”,并研究了他们对可能自我的叙述方式,和他们成熟程度之间的关系 。
研究发现,他们的“可能的自我”随着生活的转变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这些“可能的自我”中,King 和Hicks区分出了两类——当下“最好的可能自我”(best possible self),和曾经珍视的却未能实现的“可能自我”——被称为“失去的可能自我”(lost possible self)。“失去的可能自我”也就是人们口中的那些“如果”。
King 和Hicks请研究者们做了以下两部分叙述:
1.描述“最好的可能自我(best possible selves)”我们请你想象你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有哪些事是你所希望发生甚至是梦寐以求的?想象你当下正如愿以偿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不懈努力,并完成目标。想象这就是你“可能的最好生活”,或者说,这就是你想要的开心快乐的生活。
2.描述“失去的可能自我(lost possible selves)”努力回忆你曾经想象过的未来,假设一些过去的失败和遗憾不曾发生。有哪些事是你曾经希望发生甚至是梦寐以求的?想象要是这件事没有失败,而是实现了,那就是你曾经所能想到的“最开心快乐的生活”。(备注:一些唐氏综合症儿童的家长在这个环节叙述了假如自己的孩子没有患病的生活,一些同性恋者描述了假如自己是异性恋的生活。)
随后,研究者测量了这些被试的成熟程度。他们用主观的幸福程度(subjective well-being)和复杂度(complexity)来评估一个人的成熟度。
主观的幸福程度很容易从字面上理解,研究者采用自我报告式的问卷进行测量。
而复杂度则是通过测量自我发展水平(ego development)进行研究。自我发展水平是指一个人对自身及世界的体验能够到多复杂的程度(the level of complexity with which one experiences oneself and the world, loevinger, 1976)。研究者们认为,ego的本质是一种“掌控、整合、理解生命经历/体验的努力”。随着ego发展水平的提高,个体认知框架随之变得复杂。
例如,ego发展水平较低的个体,只能提出和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而那些发展水平较高的个体,则能够领悟到更复杂的人生智慧,也能够明白那些重大的生命问题往往有很多种(均为)正确合理的答案。
研究结果显示, 在叙述的过程中,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好的可能的自我”——也就是关注现在和未来还有可能实现的“最好自我”的人群,在主观生存质量的测量中得分更高,也就是说他们感到更幸福。而那些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描述“失去的可能自我”、无法释怀过去未曾实现的目标的人,则有着更低的主观生存质量,感到更不幸福(看,总想着“如果……就好了”只会让你更不开心呐)。
而另外一个研究结果是,对“失去的可能自我”叙述得更加详细的人群,在自我发展水平的测量上得分也更高,这些人有着更复杂的认知框架,能够对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 。越能细致描述“失去的可能自我”的个体,他们的自我发展越成熟,意味着他们坦然接纳失去。研究者说,真正意识到自己过去有哪些遗憾,面对这些遗憾和不可能实现的期待,是需要成熟的;同时,面对遗憾这个过程本身也会帮助一个人的成熟。
主观幸福程度和自我发展水平(人的复杂度)和人们看待“失去的可能自我”的方式之间存在相关。
研究者看到,那些目前主观报告的幸福程度较低,但是自我发展水平(复杂度)较高的人,能够非常详细地描述过去失去的可能自我,但他们却倾向于使用负面的词语例如失败、愚蠢来描述自己。这些人能够逼迫自己残酷地直面所有失去,但因为缺乏自我关怀,而只能从这种面对中或者负面的感受和情绪。
而目前主观幸福程度较高,自我发展水平也较高的人,则能够从失去的可能自我中,获得一种深刻的“感恩”情绪。例如,这样的唐氏综合症患者的父母,对拥有一个患病的孩子的描述,充满积极情感,“他在我眼中是完美的”、“他带给我的和任何不患病的孩子一样多甚至更多”。他们能够从失去的可能自我的经历中,领悟到复杂的生命智慧,从而感到平静、对遭遇怀抱感恩。
主观幸福程度和自我发展水平的改变也许比较困难,我们却可以先改变自己叙述“失去的可能自我”的方式。在你改变叙述的过程中,你已经在走向成熟。
探索“可能自我”需要注意什么?
Erikson认为,自我认同的形成源于我们对自我不断的探索。尽管大多数时候,我们认为自我在成年早期或是青少年时期(自我同一性形成时期)就已经定型,但对于“可能自我”的探索却使得自我的发展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后仍然得以延续。
通过叙事的回顾,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如何随着外在的环境和自身的经历渐渐改变的,哪些“可能的我”塑造了过去的我,哪些“可能的我”将成就现在和未来的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肯定自己曾经付出的努力和改变的勇气,并重新聚焦当下。
但是,在探索“可能自我”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才能在面对那些“失去的可能自我”时,不被遗憾和懊悔压垮。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在那些改变了我们人生的经历面前,自己是那么的渺小脆弱。
King和Hicks 认为,开始探索“可能的我”需要做好这些准备:
1.意识到麻烦不可避免。Bruner (1999) 指出,我们人生经历中的那些纷扰或失序才是每个人生命故事的主线。这些困难和挑战不断激励着我们做出改变,实现人生的转折 (turning point)。因此,在探索“可能的我”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回顾那些我们曾经遇到的麻烦。这种回顾也许并不愉快,但是必须。
2.接受“意外”。尽管我们常说,不可预见性和未知都容易让人焦虑不安。但是成长就是一个不断打破常规遇见未知的过程。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生活中的这些“意外”才让我们真正得到成长 (Loevinger, 1976)。过去经历中的种种“意外”,也许让我们失去了某些“可能自我”,但也让我们也得到了现在的“可能自我”。
3.谦逊。能够接受生活的“意外”,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不再认为自己对生活了若指掌,也不再简单地认为凡事皆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能对生活抱持一种谦逊的态度。也是这种谦逊的态度,让我们不再认为所有的得到都是理所应当,也不再对失去耿耿于怀。
4.勇气。回顾过去可能会让我们看到那个笨拙的自己,所以我们说,自我探索需要勇气。尤其是在努力回溯那些失去的“可能的我”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后悔/挫败,我们需要有勇气去赋予那些“失去”以意义。
之前有一个粉丝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说,觉得成长就是一个“可能性不断坍缩的过程”。从今天的文章来看,ta说的是准确的。每一个现在的我们背后,都有无数个失去的可能自我,因此,成长的过程,不仅仅是获得的过程,也是需要处理很多丧失和哀恸的过程,和过去的梦告别,和不再有机会尝试的可能性告别。
但我想,这种可能性的不断坍缩是值得的。正是在这个坍缩的过程中,一个更清晰的“我”的形象才得以显露;而虽然一些更广阔的可能性失去了,我们却仍然可以沿着更深、更远的维度挖掘出新的可能性来。而此时,不确定的痛苦感已经显著降低,这种可能性的发掘更像是让人兴奋的冒险——这就是在已经确定了一部分自我身份之后的探索。要想获得自我身份,就必须let go 那些失去的可能自我。
今天的文章也告诉我们,要想获得高的主观幸福感,你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现在和未来的可能自我上,详细地想象那个可能的你会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何种状态。这种想象同时也会给你提供持续成长的动力。
那么,不如留言告诉我们,你现在最显著的可能自我是什么样的?你会怎么叙述五年后那个可能的你呢?
References
Block, J. (1982). Assimilation, accommod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Child Development, 53, 281-295
Bruner, J. (1999). Narratives of aging.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3, 7-9
Brunstein, J.C., & Gollwitzer, P.M. (1996). Effects of failure on subsequent performance: The importance of self-defining go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395-407
Carstensen, L.L., Fung, H.H., & Charles, S.T. ().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and the regulation of emo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lif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7, 103-123.
King, L.A., & Hicks, J.A. (). Narrating the self i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mplications for maturity.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3(2&3), 121-138
King, L.A., & Hicks, J.A. (). Whatever happened to “what might have been”? : Regret, happiness, and matur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7), 625-636
Levenson, M.R., & Crumpler, C. (1996). Three models of adult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39, 135-149
Loevinger, J. (1976). Ego development: Conceptions and theori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Markus, H., & Nurius, P. (1986). Possible selv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954-969
Mroczek, D.K. (2001). Age and emotion in adulthood.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87-90
Mroczek, D.K., & Spiro, A. (). Change in life satisfaction during adulthood: Findings from the Veterans Affairs Normative Aging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189-202
Ruvolo, A.P., & Markus, H.R. (1992). Possible selves and performance: The power of self-relevant imagery. Social Cognition, 10, 95-124
Vaillant, G.E. (1994). “Successful aging” and psychosocial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a 45-year study. In E. H. Thompson (Ed.), Older men’s lives (pp.22-41). Thousand Oaks, CA: Sage